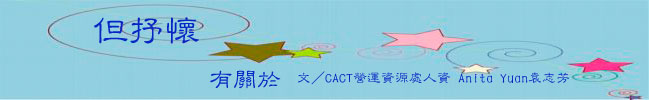
有關於什麼,有關於記憶裡的東西太多了,雙手敲打鍵盤,總感覺有些懊惱,其實題材前不久就在心裡醞釀著,可有些真實的感覺就是抓不到合適的文字來敘述,一些記憶,點點滴滴,彷彿已是一條已斷線的珍珠手鏈,灑落一地,一顆一顆拾起,拴線時才發現少了一顆;雜七雜八,又猶如是一張失落已久的拼圖,班駁無序,一張一張組合,拼到最後才發現少了的一塊,我要花時間去尋找 。
我在找,在找,可有些已經丟失的東西,遺忘已久,真的就再也找不到了……。
算了,不完整就留下一些遺憾。
再次重溫兒時的一人一事一物,或叫人心酸;或叫人留戀;或叫人沉悶;或叫人感動;或叫人疑惑;或叫人驚喜。有這些已足夠,就讓那顆丟失的珍珠、那張丟失的拼圖,在某個角落裡漸漸蒙上細灰,幽暗寂靜。
我想,有些記憶是要塵封的。
--寫在篇首
關於「神位」
「天地君親師位」是舊中國家庭中供奉的「神位」,在我們那裡是每戶人家都有的。
記得爺爺家正廳的牆上也供奉著這樣的神位,那是一張寫春聯用的紅紙,長大約是100CM,寬大約是60CM,從正中間自上而下寫著「天地君親師神位」,兩側還有一副對聯,「金爐不斷千年火,玉盞常明萬歲燈」,正對紙的左邊,從左到右是「*氏先祖」,「趙公元帥」,正對紙的右邊,從左到右是「灶王府君」,「觀音大士」。我見過的神位有的還要在左邊寫上「公元**年**月**日,有的神位,就在「天地君親師神位」的左邊寫上「流芳百世」,右邊寫上「萬古長青」,然後寫上家族成員的名字。
神位不是鐵定一律的,它是有些差異。神位下還要擺放一張桌子,放上財神爺和觀世音,還有香廬。遇上每年的春節,清明年,中秋節,鬼節,要燒香, 還要殺雞,然後將一些沾血的雞毛粘在神位上,以拜神祭祖。
還要殺雞,然後將一些沾血的雞毛粘在神位上,以拜神祭祖。
每到年底,爺爺都要將神位重寫一次,還要寫春聯。
爺爺的毛筆字寫得非常漂亮,左鄰右舍的神位和春聯大多是爺爺寫的,爺爺也很樂意。而我都會跑過去幫爺爺牽紙拿墨;那時候還沒上學前班,爺爺就教我識字,認識最早的就是神位上的字了,至於對聯都能背出來。二叔考我,我總能回答上,爺爺直誇我,那時候總能因此而得到糖果之類的獎勵,心裡高興極了。
寫神位也有講究的,爺爺告訴我,「天地」二字要寫得很寬,取天寬地闊之意;「君」字下面的口字要封嚴,不能留口,謂君子一言九鼎,不能亂開;「親」字的目字不能封嚴,謂親不閉目;「師」字不寫左邊上方之短撇,謂師不當撇(撇開)。
「天地君親師」的排序也是有講法的。「天」、「地」排前,這是因為敬畏天地,拜祭天地,合情合理;「君」是對於天授神權的皇帝,也要誠摯的去膜拜;對於已經故去的「親」人也要拜,那是表示子孫不忘記祖先;「師」是「傳道授業解惑」的先生,還是要去拜。
那時的我似懂非懂。寫好後爺爺就會問我怎麼樣。聽到我說好的時候,爺爺就會高興的笑起來,要我去拿漿糊,認認真真的貼上,並仔細欣賞一番。
對於立神位,我想這並不是迷信,這是人們的一種人生信仰,它反映出人們對五者神聖的敬仰和崇拜。如今對於「神位」不僅是用來拜神祭祖,而且是家中不可缺少的裝飾物;賣的都是玻璃裝飾的神位,講究精美、氣派,背景仍然是紅色。
只不過玻璃裝飾的神位,除了懷著赤誠和敬仰的心拜祭它,似乎少些什麼了……。
關於「米豆腐」
好想吃家鄉的米豆腐。請原諒我的開門見山,直抒胸臆了。
兩年多沒吃到媽媽做的米豆腐,真的很想吃。在深圳,朋友們一說起自己家鄉的美味小吃,我就會介紹米豆腐給她們,並繪聲繪色的講解如何製作,味道怎樣。有的時候講著講著,自己都在嚥口水了。不過深圳這邊是沒得賣的,我跑到過很多地方問都說沒有,這真是一件叫人掃興的事情。
米豆腐可以做主食,還可以做成菜。它有著濃濃的米香味,軟而且潤滑,用來招待親朋好友是首選的食物。每到快要過年的時候,媽媽就會空出時間來做米豆腐。這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樂事,有時候鄰居幾戶人家一起做,有的打井水洗石磨,有的忙著洗大鍋,有的忙著拿柴火……。孩子們都會過來玩,大一些的孩子都會幫大人拿東西,跑過來跑過去的,那情景現在想起來都有樂趣。
 製作米豆腐程序很簡單,只要掌握基本的要點就要以了。首先要將浸泡兩到三天的稻米磨成米漿。那時候沒有電磨,需要用石磨將稻米磨碎。石磨有兩個磨盤,圓圓的磨槽;三角形的磨架,磨嘴下面放一個木桶。
製作米豆腐程序很簡單,只要掌握基本的要點就要以了。首先要將浸泡兩到三天的稻米磨成米漿。那時候沒有電磨,需要用石磨將稻米磨碎。石磨有兩個磨盤,圓圓的磨槽;三角形的磨架,磨嘴下面放一個木桶。
媽媽和姑姑兩個人磨米,我覺得好玩,就跑過去吵著要把磨,媽媽看到我黑乎乎手不讓我做,我就會鬧。姑姑就會打一些水來把我的手洗得乾乾淨淨。
我那時候個頭都沒石磨高,姑姑就把我抱到凳子上。這可樂壞了我,媽媽把磨柄的上端,我把磨柄的下端。磨起來很累的,媽媽更辛苦,她一隻手磨,另一隻手拿著芍子乘著米往磨嘴裡放。有時候媽媽放多米了,磨起來就會很重,然後媽媽就舀些水進去,「吱喳吱喳」的,磨出來白白的米漿順著磨片裡流淌出來,然後從磨溝中慢慢流到磨嘴,一直流到木桶裡。
看到桶裡的米漿越來越多,心裡就越高興,媽媽隔一下陣子就會問我累不累,然後就停下來換一隻手。
有的時候磨柄太滑了,我老是抓不隹,媽媽告訴我洗濕手,這樣把得很緊,磨起來就好多了,媽媽誇我磨得好,我就會更加用力磨。
第二件事就是要燒一大鍋的開水;為了統籌時間,媽媽通常是在磨米前就準備好--洗乾淨鍋,然後倒兩桶水。燒水一定要用柴火,因為這樣火候才夠,做出來的也特別香。
在戶外燒水,這也是我們最盼望的了。哥哥是最勤快添柴;我磨一會米圖個新鮮,又會帶著妹妹一起烤火。冷風一刮,火苗就竄得很高,站在那裡一點都不冷,臉蛋都會烤得紅紅的。當然我們早已準備了幾個大紅薯,一直不停的問:媽媽,好了沒,可不可以將紅薯放進去啊?
媽媽笑著說:現在扔進去會被大火燒壞的,要等到柴燒成木炭後再把紅薯放進去,慢慢烤才行。
我們就一直乖乖的等著,幫媽媽拿東西,幫哥哥添柴火。等燒開水後,哥哥將米槳放入鍋裡燒熱,媽媽就一邊用力攪拌,一邊加適量食用鹹。煮熟之後,媽媽用大杓子將米豆腐舀入特製的豆腐箱裡(用來裝豆腐的),我和妹妹迫不及待的將紅薯扔到碳火裡,又跑到媽媽那裡問什麼米豆腐什麼時候可以冷卻,因為當米豆腐冷卻後,上面有一層米粉皮,掀起來之後還可以像北方人一樣捲起來吃,通常我們中間放的是炒好的菜,吃起來香極了,不過媽媽不准我們全部掀掉,因為掀掉米粉皮後,米豆腐容易「醒」(壞)。
放在豆腐箱裡的米豆腐都是第二天才能吃的。冷卻之後成團狀,像水豆腐一樣,不過比水豆腐硬一些。
媽媽用刀劃開成一大塊,再把細線拴在凳子或其他傢俱的一腳上,然後用細線把米豆腐劃成1至2立方厘米的小顆粒,再放到清水中。媽媽打的很均勻,然後撈起來,倒入已燒開水的鍋中,加上辣椒粉,香蔥、味精、醬油、薑絲等自己喜愛的佐料。
每次媽媽都要根據兄妹三人的口味放入荷包蛋,肉絲、香菇、菠菜等。味道或清香嫩滑,或酸辣可口。
煮的時候特別要注意時間。我通常是把米豆腐煮開了,而且顆粒打的或大或小的。不過這不影響我煮米豆腐的熱情。放入自己喜愛的佐料,還是吃的津津有味的。
又到年底,是否可以吃上曾經的米豆腐?
關於「紅花草」
冬天,寒風凜冽,大雪紛飛。在乾枯的稻茬之間的田野中,星星點點紅花草,生機勃勃。
紅花草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「紫雲英」,因為開著紫紅色的小花兒,所以我們就叫它紅花草。
在以前,紅花草是非常好的綠肥。那時候化肥也比較缺少,而且也很貴,所以每當將水稻收割完後,就把種子灑進田中;有的當水稻就快要收割的時候就灑入田中,收割水稻的時候,田地裡就昌出小小的紅花草。在收割水稻的時候不用擔心會把它壞,第二天,它就會仰起頭來。紅花草也不用去管理,只要把種子撒下去就可以了。
春天的時候,紅花草雨後春筍般地生長著,嫩嫩的紅花草遠遠望去,綠油油的一片,給田地舖上了一層嚴實、柔軟的綠毯。

小時候,一放學就和夥伴們在這片綠毯上奔跑,打滾。跑不動時候就躺在花海裡,呼吸著花的芬芳,草的清香,還有旁邊剛翻過泥土的氣息。一會兒又追逐打鬧起來,遠遠聽到有人在喊:「誰在我家紅花草地裡玩?等下把你們抓起來。」
我和夥伴們趕緊跑,而且還要摘一把,大膽的插在水瓶裡,擺在家中書桌台上。媽媽問我起就說是夥伴〔艷〕給,她家有好大一片紅花草,因為我家是不種紅花草的。雖然只是一束紅花草,但爸爸媽媽「警告」過不許破壞別人家的紅花草,如果知道是我親自摘的,在他們的眼裡會是多麼的不像話啊。
記得小學初一的時候陳老師佈置一篇作文,內容是寫一篇自己喜愛的植物,重點要以物喻人,讚美人類高尚的品格。有的同學寫的是小草,有的同學寫得是家鄉的油菜,有的同學寫的是梅花,而我寫的就是紅花草。那篇文章寫得很認真。現在回想,作文大概內容寫的是紅花草沒有被天寒地凍所屈服,頑強地挺立在風雪之中,為大地上塗上了生命的綠色,以喻人類不畏困難,頑強拚搏的精神;百花爭妍,紅花草無意爭春卻扎根生長,以喻人類謙遜不攀比的性格;到插秧的時候,農民伯伯犁田的時候將它翻入土中,被水浸泡形成綠肥,紅花草沒有任何怨言,默默奉獻自己的生命,以喻人類的為民服務,無私奉獻精神。下午兩節作文課,我一節下來就寫好了。
陳老師把這篇《紅花草》作為範文在班上朗讀。作文本在班上「跑」了二三天,那時候心裡有點害羞之外更多的是高興和小小的成就感。
紅花草開花的時候更好看,每個節上是一朵花,每朵花一般有9到10個花瓣,散發著清香。紫紅色的花兒,伴著晚霞,清風吹過,跳躍著火苗般不熄的生命力。湖畔的春柳婀娜多姿,田畦上的油菜花散發著醇厚醇厚的幽香,燦爛的金黃。油菜花的一邊就是是大片大片的紅花草,迎風起舞,伴著泥土的清香,蜜蜂的親吻,還有孩子們的歡笑……。
一年一年的過去了,現代的化學肥料早已代替了紅花草,只是在某個冬季,我又行走在家鄉那片廣闊寂寞的田野中,凜冽的寒風呼呼掠過,心裡有種淡淡的哀傷。我怎麼也尋不到那生機勃勃的紅花草了,哪怕是一小塊,甚至是一朵。
誰能再「送」我一束紅花草呢?
關於「乞丐」
最初印像中的乞丐,都是衣衫襤褸,背著一個破舊的布包,拿著一個缺邊的瓷碗,每家每戶的去討米,家裡人稱之為「討米的」。
每當小孩不聽話的時候,大人總會用嚇唬的口吻說:再不聽話,等下叫討米的把你抱走。然後小孩子安靜的坐在大人的身邊一動也不敢動,有的甚至要大人抱著,把頭鑽進大人的懷裡,直到大人說,討米的走了,小孩才探出小腦袋。這招對於小孩子幾乎是百試百靈,我也是其中的一個。
長大一些的時候,記得很清楚,每次有討米人來了,奶奶總會從米缸中滿滿的裝一碗給他們。對於殘疾的老人來乞討,奶奶總會給多些。他們一邊打開米袋,一邊操著我根本聽不懂得話,向奶奶比劃,有的還會唱上幾句,大概是祝發財之類的話以感謝奶奶的善心。當殘疾的老人一瘸一拐的離開時,我都會發現,奶奶渾濁的眼中不斷泌出淚水,然後不住歎氣說他們有多可憐……。
上小學的時候感覺討米的人更多了,有的甚至是年青人;特別是年底的時候,有的是夫妻倆,一個拉二胡一個唱戲,有唱《夫妻雙雙把家還》的,也有唱湖南著名的花鼓戲《劉海砍樵》片段,這時候你再裝米給他們,他們會不要,隨後一串早已編好的吉利話像放鞭炮似的脫口而出。
很明顯,他們只要錢。也難怪,雖然同樣是乞討,但他們是先給你唱上一段,說他們是江湖賣藝也行,好歹他們乞討方式確實是升級了。
有些鄉親為了不嚇到孩子,便一毛,五毛的打發他們走。而有的鄉親碰到給米不收的,乾脆不理他們,讓他們一個勁的唱下去,自己張羅家務事去了;大些的孩子就會跑過去聽,嘻嘻哈哈的
。
碰到這樣的主人,討米的人(這種稱呼似乎不再適合,但鄉親們還是這樣叫的,我也還是這樣稱乎他們吧)也會一直唱下去。有的主人實在沒辦法,還是給他們一些錢;有的脾氣很火的人乾脆吼起來,把他們趕走。大些的孩子又紛紛跑回家,把門關好,
討米的人又跑到鄰村去乞討。
 初來深圳的時候,才發現乞丐更多,車站旁、天橋下、馬路邊。走過一條不到200M的街道居然看見有5個乞者
。
初來深圳的時候,才發現乞丐更多,車站旁、天橋下、馬路邊。走過一條不到200M的街道居然看見有5個乞者
。
網上有人諷刺說:「10年前,乞丐是單獨行動,10年後,乞丐也有自己的組織(丐幫),金庸的小說已經變成現實。」
笑過之餘,感覺確實有幾份道理。
乞討方式也形態萬千--有的乞丐拿著碗在人群中述說自己的悲慘經歷乞求別人的施捨;有的乞丐四肢殘缺不全的在路上艱難爬行;有的乞丐乾脆就將一個破碗擺在路邊,前面寫了幾百個粉筆字靜靜的等待好心人的施捨;有些是七八歲的孩子帶著另一個熟睡的、更小的孩子,其內容都是父母雙亡,流浪至此;有些是婦女帶著小孩子,其內容是丈夫做生意虧本,拋下母女跑了,現在連回家的車費都沒有了
。
記得在龍崗看到過一個穿著比較乾淨,四肢健全的大男生,他正在攤開一張寫滿了毛筆字的大紙,開始他的乞討「工作」,標題是:媽媽,我能為你做些什麼?
他是為其母籌錢治病,紙上還附有一張某某醫院開的病歷證明。
碰到這些乞討者,難以分辯孰真孰假,教我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施捨與否?總覺得不好--施捨吧,朋友的口吻像極了閱歷豐富的老者:算了算了,別給了,現在一身破爛,等下他一下班就是西裝革履了,你還在為買一雙襪子跟人家討價還價呢。
就在我猶豫不決的時候,朋友還要加一句:不聽老人言,吃虧在言前。大有一副吃過的鹽比我吃過的飯要多,走過的橋要比我走過的路還多的樣子。於是我就在半推半走的時候將錢收了回來。
去年的時候,和同事一起在外面吃火鍋。冬季的火鍋生意特別好,人很多。客人一坐下去,推銷啤酒的女孩,帶著吉它唱歌的女孩,端著破碗乞討的老人。一桌一桌的提出是否需要「服務」。
在我們快要吃完回公司的時候,有一個帶著二胡的老乞丐,在一旁拉著二胡,穿著一件很髒衣服,一雙露出腳指頭的破鞋。
冷風一吹過來,我不禁打了個寒顫,我拉緊衣服。
老者還帶著一個破舊的布包。
對於這位老人家的外貌我就不再描述了,也是多餘的,乞者都是這樣子的。
想給他錢,而後又想起朋友的話: 算了算了,別給了,現在一身破爛,等下他一下班就是西裝革履了,你還在為買一雙襪子跟人家討價還價呢 。算了算了……。
過一會,另一桌人走了;老人家小心翼翼的放下他的二胡,看得出那是他唯一值錢的東西。然後從破爛的包中取出一個用膠袋包好的東西,他慢慢的攤開。我仔細一看,原來是一根油條,硬梆梆的。老者嚼了一口,用力的往嘴裡咽。晚上10點多了,他還沒吃晚飯。
同事將鍋裡一些青菜乘給老人家的碗中,然後又倒了些酒,並說:老人家,喝些酒,暖暖身子。
老人家連連道謝。他吃完後,收拾好東西,站起身來拿著二胡要給我們這桌拉上一曲。我們都知道這是他唯一能表達他的感激之情,我們都說不用了。
這時,我分明感覺自己的眼淚快要流出來了,我從口袋中拿出零錢,走到老人家身邊,遞了他,沒有再想他是否現在一身破爛,等下他一下班就是西裝革履了什麼的了。
老人家抬起頭,接過我手中的錢,激動的說了聲:謝謝。
隨後幾位同事都給了些零錢給他,老人家道謝離開。
寒冷的冬季,我真實的感受到了人心的溫暖。
而對於乞討者該不該給予施捨這問題,我也沒敢深入去思考過。有人說乞丐是出賣自己的尊嚴得到了金錢,我們不要亂用自己的同情心;有人說不管在哪個國家總會有這樣一個貧窮孱弱的群體,我們應該給予幫助。
今年11/23日的《南京都市報》報道「乞討得來100元,乞丐轉手捐病友」,殘疾乞丐陳春偉的舉動感動了廣大市民和網友,這一事件又帶給我們太多的思考了
。
怎麼面對乞丐?畢淑敏的一篇《坦然走過乞丐》,感受很深:「朋友說,要有正式的慈善機構來負責這些事務。它要接受各方面的監督,來有來路,去有去路,一清二白才能把好鋼使在刀刃上,又省了普通民眾的甄別之難。從那以後,我可以坦然走過乞丐身旁。對於那些慷慨解囊之人不再仰慕,對那些揚長而去之人也不再側目。當然瞭解,也積極向正規機構捐助並期待他們的清廉。」
--The end--
關於所寫的一切,是自己的一種信仰?是家鄉一種文化?是一種長大後的感悟?還僅僅只是一種單純的懷舊?我不確定,我只知道這種感覺如此美好,如此讓我眷戀,真想永遠把自己置於這種安靜溫暖的記憶中。
時間匆匆忙忙,晃晃悠悠,2006要過去了,那麼就繼續讓回憶在時間裡沉澱,正如時間在回憶裡消失那樣吧。
--寫在篇尾
2006年12月10日
[回上層目錄]
除商業用途,歡迎轉載。
轉載時請勿更改、刪減、或增加任何文字;並請註明出處。
以上文字或圖片若有侵害到任何人的權益,請來信至dcc@act-ioi.com.tw。